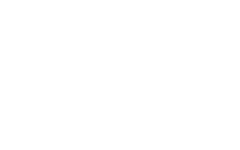- 2024-06-15
- 浏览量:749
TEDxSHBS Youth
“
对于以前的我而言,抑郁一直是一个很遥远的词汇。从小到大身边但凡出现同龄人伤害自己的情况,一定会被评价为“玻璃心”或是“养大了也没用”。所以,抑郁到底是什么? 是一种矫情的、⻅不得人的病。但这是正确的定义吗? 迷惘与无措总是笼罩着我。

直到有一天我习惯性打开了看理想的播客。播客的讲述者夕阳拥有传统意义上幸福美满的生活,父母开明成绩优异。学着临床心理的她却在大三的尾声开始解离,确诊重度抑郁。没有曲折离奇的故事,就这么确认了。听完这两期长长的播客,我才第一次真正意识到,“我可能有抑郁症”。尽管这已经是我心里最深的一铲子,我也只是怀疑了0.01秒。因为我的环境,身边的所有人都告诉我,这不可能。

我今年17岁,四年前的某一天,我的感觉消失了。清晨的阳光照常撒下,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声⻋声如常。我却突然什么都感受不到了。
仿佛我的一切感官都被按了暂停键一样。这是我躯体化的第一次发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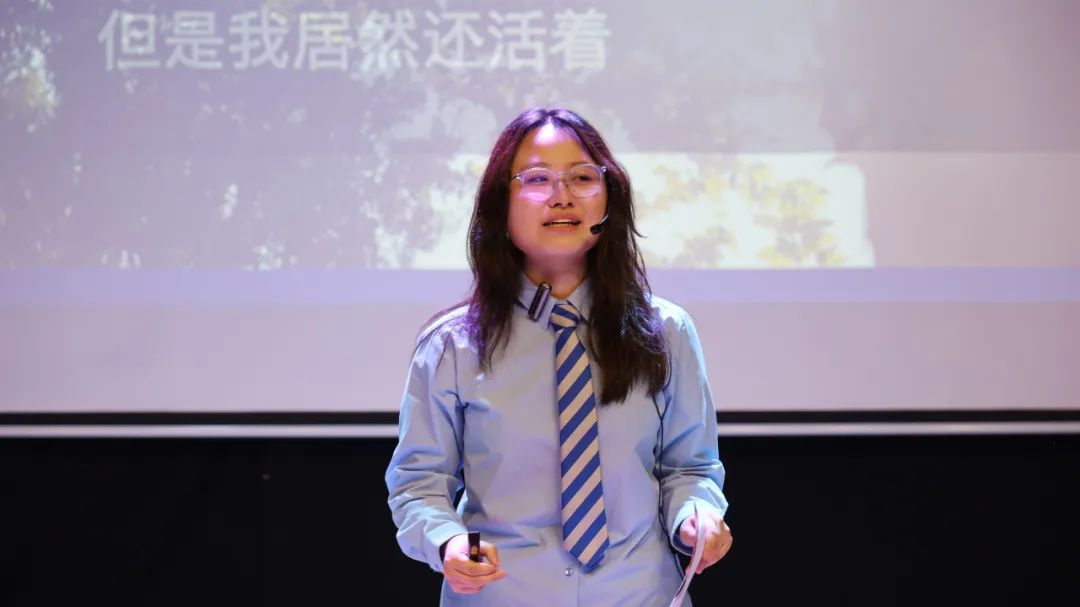
感觉消失的症状断断续续持续了半年后,我终于鼓起勇气和妈妈讲了这件事。不出所料, 妈妈只是轻飘飘地抛下了一句“不要每天想那么多,心思放在学习上。”希望落空的感觉太熟悉也太痛心,仿佛被细细密密的针一点一点扎着。初中时我从未拥有过锁上甚至关闭房门的权利,按照我父母的话就是我没有资格有隐私。因为我还小。他们的爱包裹得我窒息。
我当然知道他们都爱我,给我最好的并且牺牲了很多很多,为了陪我上学,住在阴暗狭小的出租屋里。我也很爱他们,但有时家庭关系就是一团缠在一起全是死疙瘩的毛线,永远都说不清楚。我最恨白眼狼这个词,捆在每个“我”的脖子上,被名为责任的东⻄束缚一生,所以呢,为什么不允许逃离,为什么呢。

每当我放学回家,书桌上可能会随机刷新出前一天藏起来日记本,或是偷偷新打印出的戏剧剧本,书桌旁是面色凝重的妈妈。我曾在日记本的最后一页写过一封很长的遗书,她看到后慌极了,对我说道: “爸爸妈妈只有你一个孩子。你不可以死。你要对我们负责。” 是啊,责任。我没有资格去死。我不能,也不会生病。
整个初中三年我都活得很压抑,学校是标准的衡水式学校,五分钟的吃饭时间,早七晚十, 一周六天课的魔⻤作息,周日也排满了课。下课不学习就会被认为没有上进心,整个大环境都在教我们不要关心他人,只有变得更漠然甚至是PUA别人才对自己有好处。从学校到家里,摄像头无处不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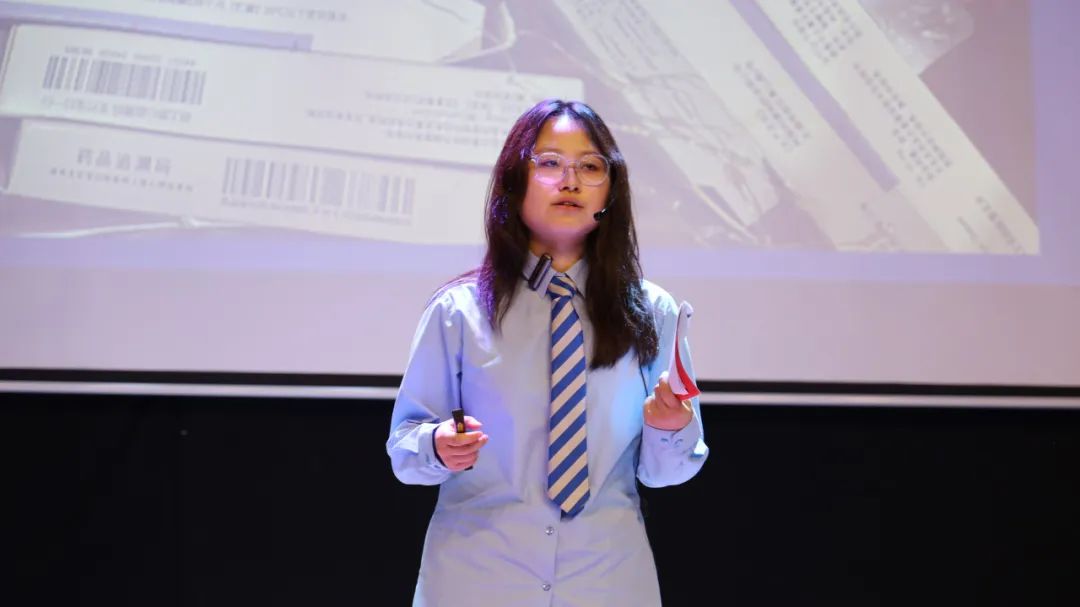
中考前夕崩溃到几近解离的我把自己锁进厕所,只记得当时躯体化的麻木把我的全身都包裹住了,从头顶、脖颈、脊椎、手一路麻到了脚后跟。我也不确定是否是我的大脑篡改了这段记忆,因为那三年里的很多东西都被潜意识封存住了。这是我第一次离死亡这么近。
但一个睡着的人一旦被叫醒,就再也无法真正沉睡。装睡是一个痛苦而漫⻓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思维模式与价值观被我所读的书、社会新闻以及周身发生的事情逐渐建构,不断地揉碎又重组。这三年我一直找不到自己活着的证据,因为根本感受不到与世界的链接,仿佛我只是一个按照程序运行的NPC。为了让自己不再麻木,我会拼命搜索边边⻆⻆的社会新闻来提醒自己,不要变得漠然,这个世界不是乌托邦。书本、戏剧、电影、新闻,变成了我与世界链接的唯一渠道。

中考结束了,我不出意外地发挥失常了。改志愿的时候我做出了人生中第一个属于我自己的选择,我选择了扬州中学的国际部。父母得知后大发雷霆,这也是我第一次逃离他们给我划定好的人生路线。这个走出体制内的决定相当于提早四年消失在他们的掌控中。冷战的两周中他们不得已接受了我试图摆脱束缚的事实,开始研究AP课程如何内卷。对于他们来说,国际部是拿不出手的,只有走捷径的人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所以周围很少有人知道我并没有在上普通高中。这是我最难捱的一段时间。中考后我更加焦虑与疲惫了,我以为会好起来的一切都没有任何改变,反而变本加厉。胃痛变成了家常便饭,也经常做出一些伤害自己的行为。有次被妈妈抓到,她问我要一个解释。她认为我伤害自己不仅是对我不负责,更是对她不负责。冷战持续了三天后终于爆发了剧烈的争吵。我至今还记得她失望的眼泪与不可置信的眼神,仿佛在告诉我,我没救了。

确实,这一年我过得混混沌沌,半体制内半国际化的课程令人心力交瘁,不断严重的躯体化使我的腰椎肌肉僵死,持续性心悸折磨我到窒息,生理期则整整断了半年。有时候课上着上着我会冲进卫生间大哭抽搐,考试也时常惊恐发作。是的,我完全不知道我的情绪是什么样的了。我休学了。我花了整整四年,将近我人生中四分之一的时间,去证明我生病了。
故事讲到这里,我却无法责怪任何一个人。我无法责怪我的父母。他们接受的教育使他们没有抑郁症的概念,我周身的环境则极其排斥和主观情绪挂钩的一切。
但我们是人类呀。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类。
在这之后我做出了人生中第二个重大的决定。我转学来到了上海,这次,我的父母选择了同意。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听闻了更多不同的观点,⻅到了许多与我相似的人,也终于开始见医生,见咨询师。远离父母后我的生活终于撕开了一条可以喘息的缝隙。但我的抑郁程度有变轻吗?可能并没有。治疗是一个漫⻓而耗心力的过程,内脑功能的减弱,持续性的失焦与手抖。药物使我的生活总是充满困倦的因子。很小的事情就能触发到我创伤的部分并应激,一下跌到谷底的情绪与如潮水般涌上心头的结束生命的念头总是令人措手不及。

这些东西涌上来的那一刻把人淹没至窒息。我一个人溺在情绪的海洋里挣扎,手脚到处乱扑腾,以为抓住的是救命稻草其实只是一根随洋流飘动的水草。连根都没有。我每次都在撑。撑一下。再撑一下,仿佛就能永远地熬过去。莫名其妙的恐惧与不安无时无刻不包裹着我,高敏感带来的刺激使我的惊恐愈演愈烈。
“我用意志力让自己的日常回到正轨,但我的灵魂无时无刻都在分崩离析。” 台剧《她和她的她》中患有抑郁的女主有这么一句台词,这便是我每天的状态,也是千千万万个抑郁患者的状态。失神,解离,把支离破碎的自己强行按回原位。
我时常在想,我真的接受自己停转了吗? 我真的能看到18岁的太阳吗?
我真的能撑过第五年吗?
直到我某天下午从医院出来。路边种满了梧桐树,葱葱茏茏地挤在一起。落在水泥路上的阳光碎片竟和树干上斑驳的痕迹一样,也和斑驳的我一样。
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还活着。天呐,我居然还活着。
我在十七岁这一年学会了如何正视我的情绪,并且尝试与Ta沟通。在这个世界上,我拥有一群爱我的朋友,我所热爱的事物。所以,没事的。我们是被爱的,被整个世界所爱,被不经意撒下的日光所爱,被拂过的微风所爱。尽管有时候会被孤独淹没,但请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千千万万个“你”正同你一般经历着这些,在陪伴着你。
与情绪和解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也不会要求自己去做到。每个人都有抑郁的权利。愿意去面对已经是莫大的勇气了。正如播客的标题一样,抑郁是你我共有的秘密。
我是真真正正一步一步长大的,我是无数个我中唯一幸存的我。
文 | Olga Liang(G10)
排版 | Jang
图 | Kimi Wang(G10) Thea Wu(G10)